纪念|诗人谷川俊太郎:语言的匠人,以此手艺为生
- 商业
- 2024-11-19
- 1
- 更新:2024-11-19 10:20:22
当地时间11月13日,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离世,享年92岁。谷川俊太郎是日本当代著名诗人、剧作家、翻译家。堪称当今国际诗坛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。2010年,谷川俊太郎曾受邀到香港中文大学参加“国际诗人在香港”活动,并接受了记者专访,以下为当时采访实录。

当地时间2023年4月25日,日本东京,诗人兼翻译家谷川俊太郎接受采访。视觉中国资料图
2010年谷川俊太郎受邀来到香港中文大学参加“国际诗人在香港”活动,在香港的半个多月里,他在香港度过了中国的中秋、国庆,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也同时出版了他的诗集《春的临终》。谷川俊太郎跟我们印象中的诗人是那么不同,他会很坦率地告诉你,“我写诗就是为了赚钱,养家糊口。”他也会说,“写诗与我私人感情没有关系。”“都说诗人是艺术家,但我更愿意称自己是手艺人,我是语言的匠人,以此手艺为生。”
出生于1931年的诗人谷川俊太郎是日本战后崛起的一批日本艺术家代表之一,诗人谷川俊太郎、作家大江健三郎、建筑师安藤忠雄,导演宫崎骏等等,他们在各自的艺术领域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。他们目睹战争和死亡,懵懂中接受日本战败,艰辛中重新建设国家,经历经济奇迹。然而,谷川俊太郎又似乎是他们中的一个异类,他会告诉你“我不关心历史”,不仅与历史、政治绝缘,他漫长的创作生涯也为了谋生创作无数歌词、剧本、广播剧,中国读者熟悉的《铁臂阿童木》和《哈尔移动的城堡》主题曲均出自他的手。此外,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式,他是其中的艺术指导,相关纪录片《东京奥林匹克》剧本也是由他撰写;1970年大阪世博会,他也是艺术指导,同样参与同名纪录片的剧本写作。他以另外一种方式,参与日本历史之中。谷川同样也不是老顽固,他说读诗的人少了也不要太惊讶,因为诗歌中诗情已经广泛存在于广告、漫画、建筑之中,而语言“就是不断变化的,谁也挡不住语言的变化。”
在他自己的 “自画像”《自我介绍》中,他如此描绘自己,有一点自嘲:“我是一个矮个子秃老头/在半个世纪之间/与名词、动词、助词、形容词和问号等一起/磨练语言生活到今天/说起来我还是喜欢沉默……我对过去的日子不感兴趣/对权威持有反感/我有着一双既斜视又有乱视的老花眼……对于我,睡眠是一种快乐/梦即使做了,醒来时也会全忘光/写在这里的虽然是事实/但这样写出来总觉得像在撒谎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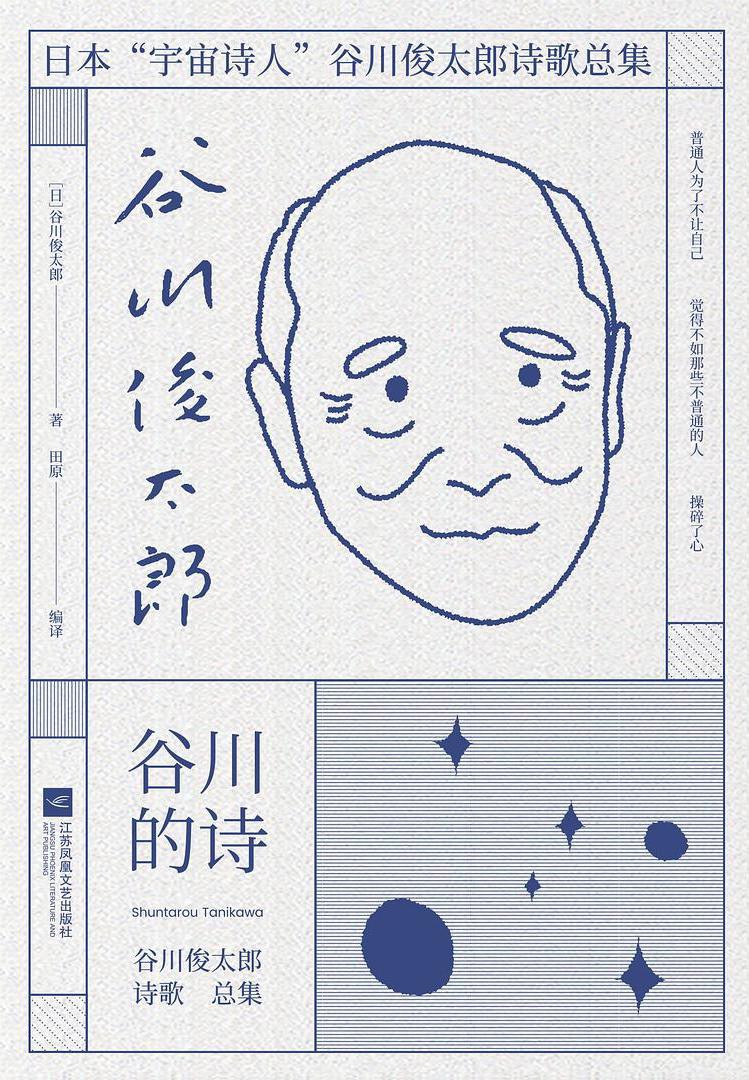
“我只是把诗歌当作商品”
记者:那么漫长的创作生涯中,你有厌倦和丧失兴趣的时候吗?
谷川:我从一开始写作就厌倦。我不喜欢写作。
记者:那你是怎么坚持到现在的?
谷川:为了赚钱,养家糊口。写作是我唯一的收入来源。都说诗人是艺术家,但我更愿意称自己是手艺人,以此手艺为生。我以写诗为生,就跟木匠、陶匠的生活差不多。我是语言的匠人。
记者:很多诗人都把诗歌当作武器使用,那你呢?
谷川:但我恰恰相反,我只是把诗歌当作商品。要是诗歌卖不掉,那我就没办法养活自己。
记者:既然是商品,你的诗歌价格在日本定价是否合理?
谷川:但是诗歌又是没有价格的,我自己不会在诗歌上贴个价格标签。我是一个被动写作者,有人来约稿,我才写诗。当然,约稿的时候,价格就已经定下来了。
记者:你会区别对待约稿写作和自发写作吗?
谷川:在我内心,约稿或是自发写作,对我是没有区别的。但我不得不承认,我的所有作品中,90%是约稿的,剩下的一小部分才是自发写的。但就算是自发写作,写诗也不是我情感的表达,我写诗是为了让读者看到,写诗与我私人感情没有关系。
记者:这样对待诗歌,有很多人肯定会很生气。
谷川:那就对了,因为我不想和别人那样。没人主张这么写诗的。
记者:你对诗歌的态度那么特立独行,但你的诗歌本身充满质朴的生活气息,读的时候让我想起的是你们日本品牌“无印良品”。
谷川:与其写诗,更重要的是生活,生活才是具体的,所以我的诗歌让人读起来,离生活还是比较近的。我与生俱来就与社会、世界保持距离。某种程度上,我也不太喜欢人。我所信任的只有大自然。作为自然一部分,女人,我喜欢。而对于历史、政治,我都不感兴趣。以前我还要为了讨生活,拼命赚钱,现在我完全靠诗歌版税就能养活自己了,真的成了无欲的人了。
记者:但是几年前,你还以模仿联合国《世界人权宣言》形式,宣告了一个你个人版的《世界人权宣言》,这是怎么回事?
谷川:这纯粹出于自己的正义感和人道主义,这里不涉及意识形态,只是普通市民应该说的话。我厌学,讨厌学校、讨厌国家,反对一切体制,这在我内心始终存在。某种意义上,我是无政府主义者。

“诗歌下降,诗情增加”
记者:在你的诗歌中,就像其他人评价的那样,你把自己作为宇宙的一分子投身其中,你同意吗?
谷川:是这样的。我是家中独生子,没有兄弟姐妹,与人接触很少。我从少年开始,就不太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而是人与宇宙的自然关系,持续至今。在这么长的人生中,我结婚、离婚,有朋友,要与出版商打交道,但就我个人来说,我与世界的关系就是宇宙。我诗歌中的宇宙感,与我与人之间关系淡薄有关。这是诗人与世界保持的特别关系。
记者:这也是你写作的创作母题吗?
谷川:如果说有什么母题的话也是隐藏起来,读者看不到,只在我内心。总的来说,我写诗就是对语言的不信任,自始至终。自己与世界、与宇宙的关系,是我写作隐藏起来的主题。对我来说,语言与自然完全对立。
记者:我想有人会批评你的诗歌太肤浅,不抽象,没有实验性,形式上更没有创新。
谷川:我不认为实验本身会产生好的作品,我自己也会去尝试一些实验性作品,但最后恰恰不是从实验中产生美丽的诗句。我也有抽象的作品,但非常少。我作品最大特点就是易读耐读。我的愿望是,能有更多人读到我的作品。
记者:你现在完全靠诗歌版税就能舒适生活,这可能是个特例,因为绝大部分诗人都在失去读者的出版市场。
谷川:在日本也是这样。但我想说的是,“诗”这个字用汉字来写,就是语言的言加上寺院的寺,“诗”这个字在日语里有两个意思,诗作品和诗情。诗作品确实在全世界都下降的很厉害,但是诗情不只在文字写得诗歌中,还存在于广告、建筑、漫画中,诗情在增加。所以,诗歌下降,诗情增加。而且在日本,就算现代诗的读者在下降,但日本传统文化中的短歌和俳句已经有广大读者,写得多读者也多。现代诗与古典诗的对立历史,但现在大家井水不犯河水,不过写古典诗的活得更好。现代诗作品在发表拿了稿费之后就没有收入了,但在日本写俳句的俳人会公开教授写俳句收取学费,收入颇丰。可是有谁会花钱去学现代诗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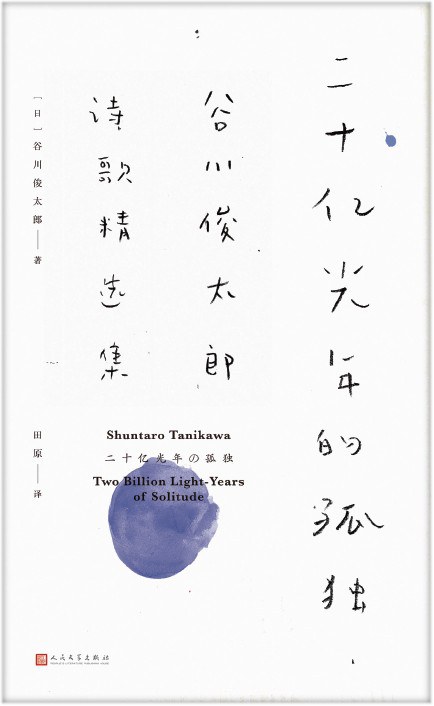
“没拿《铁臂阿童木》版税是个拯救”
记者:你也说过,为了生活,你写了大量歌词,现在还写吗?
谷川:我首先是个诗人,不是词人。我60岁以后,光靠诗歌版税就可以轻松地活着,不用再写歌词过活,所以写的很少。我年纪越来越大,写诗反而成为最快乐的事情。
记者:你最近写的歌词包括宫崎骏电影《哈尔移动的城堡》主题曲《世界的约定》,能谈谈这次合作吗?
谷川:最初是宫崎骏电影《千与千寻》主题曲演唱者木寸弓来找我,求我为他写一首歌词,歌词主题是关于失恋,但也不是失恋中的不幸。当时还和宫崎骏的电影没有关系。这首歌就收入了木寸弓的新专辑中,这张专辑卖得非常好。宫崎骏非常喜欢我写的那首歌,就希望把这首歌作为《哈尔移动的城堡》主题曲。日本的传统是,电影制作的时候,创作一首跟电影吻合的歌,现在都是电影拍完了,找一首流行的歌做主题曲。所以我的歌与电影完全没有关系。
记者:回来看过这部电影吗?
谷川:有人把我的歌当作电影主题曲了,我一定要去看一下。但是歌从电影里出现的时候,我觉得处理得不太好。
记者:你创作的《铁臂阿童木》主题曲,“越过辽阔天空 飞向遥远群星 来吧阿童木……”也是你创作的,在中国的1980年代也很受欢迎。这应该是你流传最广的歌词了吧?
谷川:那是一定的。当时来看,这是一部非常有趣的作品,现在还有孩子喜欢。
记者:到现在还带来收入吧?
谷川:当时曲子给我之后,我拼命找出和曲吻合的歌词。导演没说要给我多少钱,他很穷,白手起家,为了拍电影破产了几次,所以勉强给我50万日元作为稿费买断,但就拿了一次。那时候我调查了一下,《铁臂阿童木》在日本几乎天天播,风靡世界,如果严格按照版权付费的话,当时我每年至少有1亿日元收入。没拿《铁臂阿童木》版税是个拯救,要是我一直拿版税的话,我早就不写作了,到美国买个别墅住了。当时这首歌的作曲者,他是拿了版税的,结果可能钱拿得太多了,之后再也没有写什么作品。